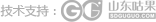拆迁制度变革:非公益性拆迁是否适用平等协商原则——私法与社会法学者的对话
赵红梅:本次高峰论坛的主题是非公益性拆迁是否适用平等协商原则。我们学校其他部门不久前办过类似的讲座,其切入点是公法与私法的对话:北京大学沈岿教授作为公法学者的代表与我校民商院刘智慧老师作为私法学者代表进行了对话。我们今天确定的切入点是:私法与社会法的对话,相信今天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思想的火花。
下面我荣幸的介绍本次论坛的嘉宾:坐在我身边的是北京大学钱明星教授,钱教授是去年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北大五教授之一,并且是其中唯一一位私法学者。这位是人民大学的叶林教授,叶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商法学者,在商法领域是很有建树的,我在参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活动中曾领教过叶教授的风采。最后一位是我校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所副所长薛克鹏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研究我国房地产法。
我们先介绍本次论坛的一些背景资料:
2009年12月底和2010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召开了两次专家研讨会,计划以新的条例来取代《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可见北大五教授的上书引起了国家立法部门的重视。拆迁一般在法学界区分为公益性征收和商业性拆迁,公益性征收是指政府只有在满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可以征收,这一点在法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对与商业性征收很多法学学者都主张这是一个民法问题,按照民法原理,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基于平等协商原则通过谈判缔结民事契约,来决定拆迁和补偿问题。我们今晚会针对这个问题来展开论辩。
下面有请钱教授就北大五教授上书的情况以及他自己的看法做一介绍。
钱明星:关于上书,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有关部门已经在着手准备对拆迁条例实施修改,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政法大学江平教授、王利民教授和我一起参加了一个专家会。但是在物权法颁布之后,这个条例却迟迟没有出台。在这期间,在湖北四川都发生了因拆迁发生的暴力事件。可以看出政府在这方面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从学者的角度讲,应当把自己的想法和有关部门做一反映。应该来讲,我们的上书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而重多拆迁户在拆迁过程中的积极的、血腥的、残酷的抗争是拆迁条例的修改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决定性原因。
客观来讲,拆迁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以低估的,在我国如此之高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里面,房地产业占到了2%左右,具有极大的贡献。同时房地产业的发展对于人民居者有其屋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不能用斯大林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逻辑来评价它。尽管有如此大的作用,拆迁对私有财产权带来的侵害时不可低估的。同时30年来快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浮躁的情绪,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例如,通过拆迁建立起来的建筑基本都是垃圾,在中国走到每一个县城,基本都是同一个模式。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的学者,都认为对拆迁应当在立法层面上加以规范。立法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区分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公益性拆迁的基本目的就是保证这种拆迁是可以强制拆迁的,而商业性拆迁只能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自愿协商,才能保证被拆迁人的利益。
赵红梅:下面请叶林教授对四十条的规定以及立法对地方政府诉求的妥协谈一下他的认识。
叶林: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复杂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公共利益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种叫显性的公共利益,一种叫隐形的公共利益。意见稿第二条涉及的危旧房改造、科教文卫建设、廉租房建设等是一个极具扩张力的解释,在所谓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几乎可以将所有的商业开发涵盖进去。所以我认为,该草案走了一条很危险的道路,就是将商业化目的转化为公共利益名义。所以在实践中对公共利益做像理论上一样的区分是做不到的。
第二,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命题上,我们理解的公共利益的应该做一个限缩性解释,公共利益的解释前提就是如何对抗私权利。所以条例带来的问题不在于公或者私的划分问题,而在于通过公共利益的桥梁实现商业开发的目的。如果这样,该条例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三:无论是城还是乡,房屋所依赖的土地有三种,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不属于拆迁条例的规制范围,第二种是出让的土地,在出让的土地上建造的房屋,第三种该土地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的。所以就城市土地来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缴纳了土地出让金的,一种是没有交土地出让金而是事实理由形成的。这两种情形下的房屋所有权人只对自己的房屋享有所有权,但是由于土地问题的特殊性,权利的含量是不一样的。如果缴纳了土地出让金,我相信你的房屋是不敢有人轻易拆除的,而真正被拆迁的往往是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即在土地使用权上有某种残缺,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房屋真是大肆拆迁的对象。所以在看待拆迁问题时,需要做细致的分类。对于第三种情况下,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就会相对宽松。但是如果缴纳了土地出让金,有70年土地使用权,用什么样的理由可以拆迁。不能因为地下矿产资源的保有就损害地面上的权利。条例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尤其要注意通过公共利益的泛化解释来暗度陈仓为商业性拆迁创造机会。如果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90%的民主制不能和公共利益相配合就会使得钉子户永远不会存在了,会更加加快拆迁的过程。
另外,被拆迁户的概念需要怎么界定?被拆迁户这个概念是很容易被调整的。在人群密集的情况下,达到90%的比例是不容易的,但是把基数放大,达到90%就非常容易。因此如果这里没有外延上的和关联度的概念的考虑,而仅仅用被拆迁人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是非常容易被玩弄的。
所以我对法律的理解就是:我们不是追求最好,只是追求相对较优的方案。
赵红梅:下面请薛教授陈述他的学术观点。
薛克鹏:我不是从私法和公法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拆迁条例对私权利的损害时非常多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其实它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也是非常大的:公共土地的流失,公共财政的滥用,最终导致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同时受到损失。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新制度建立的时候虽然需要以个人理念作为本位的理念,但是不要否认公共利益的需求。意见稿中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要么继续疯狂拆迁,要么无所作为。
关于第四十条,我认为它是一个无用的条款,因为意见稿针对的对象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但是大多数的纠纷都发生在集体土地上。对于城市来讲,我们需要考虑有多少利益是纯粹的私人利益,有多少与他人利益毫无关联的私人利益? 在中国城市中,我们的居民都是一个共同体,我们的房屋也是包括私有和共同共有两个部分。作为社区来讲,那么共同部分就可能成为公共利益。在城市里,不要把自己的产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产权,其实大家是一个共同体。如果按照纯粹的自由协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私人权益,但是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同意拆迁的比例很难达到90%。所以在城市里虽然大量的利益是私有的,但是我们处在和他人利益的共同环境中。在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人利益的实现。因此,我赞成保护个人利益,但是保护个人的利益的同时也要有所考虑,即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要有所平衡。如果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这些问题时,这个条款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我也反对政府的无端介入,尤其是要把政府的行为放在公共利益的对面,不要把政府的行为都看成是公共利益,因为经常有私人会利用政府之手满足自身的个人利益。
赵红梅:下面我们进入到深入讨论的环节。拆迁不光涉及到房屋,也要看到土地。国有土地是分类型的,包括划拨,出让和城市私房用地。请问钱教授,国家对土地有所有权,但是在拆迁过程中,需要政府靠边站,而由房屋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来同开发商进行谈判对土地行使处分权,是否可以说的通?
钱明星:第一:国家所有权的认识问题。最近在讨论拆迁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土地实行国有政策,同国外不同。但是国家所有权是什么呢?从马克思经典哲学的观点来看,国家所有权是由对私有权和剥削的否定上来建立的,国家所有权的建立表明国家本身是不应该获益的,利益应当属于全体人民。在我国却不是这样的,政府和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利益。公共财政的使用和政府的利益以及官员的个人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在论证国家所有权的时候,很多领导人都会谈到在国家财政里面国有企业占到多大成分。我国国家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无非就是两个:一、好用,政府、官员喜欢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二、好支配,国家财产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遍地都是,任何人离开了国家财产时不可能生活的。共有制国家对私人的控制同私有制国家对私人的控制是不能相比的。这就是国家所有权的异化。第二,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国家所有权的行使要靠具体的主体和制度。在英国,英国的土地在名义上都属于英王所有,个人对土地享有地产权。在我国,国家土地所有权就应当由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利把非所有权人使用土地的权利固定下来。这些权利是独立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由行使和处分,在拆迁问题上,拆迁的是房屋的所有权,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已经出让了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要比国家土地所有权享有更加优先的效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征收单位和房屋所有权人之间的关系。
赵红梅:叶林教授认为不同的土地上,权利也不一样。是否在不同类型的土地上,其中的内容例如自由会有所不同?
钱明星:从这个角度上,我不同意叶教授的看法。我认为,房屋所依附的土地使用权非常复杂。物权法使用国有土地建设房屋的权利都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些权利所承载的房屋所有权是一致的,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看,房屋所有权都是应当得到保护的。
赵红梅:房屋所有权保护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钱老师的观点在于要架空国家所有权,把私人的土地使用权坐实。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溢价归公还是归私的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听一下三位教授的看法。
薛克鹏:我同意溢价归公。这里的认识有一个误区。土地的价值的增长取决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成熟状况。土地的价值取决与周边的公共设施环境。这不是私有财产本身自己增值的,属于是基于公共投入所获得的增值。
叶林:我没有归公和归私的概念,讨论归公还是归私是一个静态看问题的看法,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我认为条例的很重要的作用在于搭建一个强制磋商的机制。通过磋商达成归公或者归私的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条例的主要内容是政府迫使存在争议的两方主体,必须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磋商。磋商的结果导致的利益的转换都再所不问。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关于归公或者归私的处理机制。平等协商在某种意义上应当称之为强制性磋商。民主制的方式是用在同质性的社会居民之中的,但是政府和被拆迁人之间不是同质性的,要么通过自愿的方式来解决,要么通过强制的方式来解决。机制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分类的方式,结果并不重要。
赵红梅:叶老师的观点我认为钱老师不会认可。非公益性拆迁并没有集团的概念,而是个别性的磋商,而不是团体性的磋商。实践中就会出现漫天要价的情形,特别是钉子户一般会比其他的拆迁户多得到拆迁款,这样的诉求是公平的吗?
钱明星:实际生活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在非公益性拆迁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尊重两个价值,一个是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一个是市场公平自愿的价值。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在此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证。一个人在一地生活所形成的和周边的关系,包括个人感情等,都是需要得到尊重的。在这种环境中,形成了一种很自然的生活,实际上尊重私人财产权也是尊重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通过外力来破坏它。如果有钉子户拒绝搬迁的时候,中国的开发商,也应当向美国的开发商一样学者绕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百姓都是善良的,我们的胃口也不是特别大,只有利益的到适当的满足,我们也是会做出让步的。所以没有必要加以更强的限制。
叶林:中国的城市、乡村都是很复杂的。美国的案例拿到中国是不合适的。我在考虑,划拨或者老的宅基地是没有年限的,形成了一个不定期的合同。物权法对住宅用地有70年后自动续期的规定,但是对于非住宅用地则没有自动续期的规定,那么在期限届满之后就收归国有。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拆迁,与在美国被认为房产是可以永久被拥有的概念是不同的。在中国,房产是永久的,但是房产依据的土地却不是永久归你使用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对私权的保护和美国对私权的保护是不同的。第二类情况是,我希望借鉴香港的90%的做法,使得钉子户的问题通过多数人的合理协商的办法得到解决。而这个规则就把一些人不恰当的预期打消掉。这里由于中国的危旧房改造和香港的改造是不相同的,中国危旧房都是棚户区,其共有部分面积与香港楼宇面积相差较大。我们要将楼宇上共同决定的原则转引到平面上,是可以尝试的。第三就是协商要价的问题。如果是商业性开发,漫天要价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就公共利益开发,政府作为拆迁的一方,群众作为拆迁的一方,这样的强制没有居中裁判者,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群众的利益受损。在搭建这种协商机制中必须有居中裁判者的功能,一个方面是动用法院的资源,另一个方面,政府为什么不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消灭被拆迁人的房屋呢?第三方面,重大拆迁政府说了算,政府负责协商各项事务。如果我们能够在平等协商之上构建司法和特殊的诉讼程序,以及立法机关功能上的机构,似乎其合理性要强于强制拆迁。直接民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间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钉子户的问题,主要在于其解决通道不畅。
赵红梅:请问薛教授,北京酒仙桥地区旧房改造的试点终于因为票选结果没有达到规定的比例最终失败,台湾地区都市更新条例规定了申请、补偿等都要进行多数决,你对此怎么看。
钱明星:我非常赞成叶林教授提到的程序设计,平等民主公开。除了香港和台湾的做法,韩国的商业拆迁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在拆迁之前会组成一个社团机构,开发商通过和社团机构谈判,遵循特定的程序,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同时兼顾城市开发的需要和私有权益的保护。
叶林:我最近一直在研究一个题目:私权利的转型。私法以个人为单位开始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一种团体私法,例如消费者协会或者业主协会等。无论是否登记,人们都会将其当成是一个共同体来看待。在这个团体中就有共同利益的存在。由于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实现个人的利益,所以要让渡一部分利益给团体,而团体则以更强大的力量对外争取个人的利益。这就是财产权利管理权或者个人权利的集体权。这与以个人为主体的私法完全不同,这就会形成一个更复杂的权利结构。这个权利结构到底是什么?是私法上的概念还是公法或者社会法上的概念。私法可以分为个人私法和团体私法,在团体私法中,团体会员的权利依然是私人性质的,所以它更像团体化的权力而非公益。如果这个结构存在,那么其磋商机制就会存在。我们非常关注个人权利的同时会发现 我们的环境已经被团体化了。这种团体不是公权力团体,但是在职能上可能发展成为带有社会职能的团体。一个组织功能可能是多元化的,但是权利应当依然是私权利。所以我非常不理解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的概念,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社会责任,但是对社会责任的概念也在争议。这二者一个是从性质上考虑,一个是从社会职能的角度上讲的,功能上一定带有某些社会化的性质。因此我觉得公共利益的界定可能有偏差,不是所有对大家好的东西都是公共利益。因此我不敢是它不是公法或者社会法的问题,但我更倾向于它是私法的问题。
赵红梅:我有一点质疑叶老师,在谈到结盟,私法和社会法还是有一点微妙的区别。如果是基于自由结盟,那就绝对属于私法。只要是没有外在强迫的,肯定属于私法。我们迎接的挑战在于社会安排和法律的安排,这还是需要引起现代私法学者的注意。
薛克鹏:我觉得叶老师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私法的角度,团体和群体有更多的自由性。但是从社会法角度,这种社会群体不是由于个人一致决定,而是基于社会化分工和连带关系形成的,既不可以随意退出,也不能随便加入,形成了一个理由共同体。这不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每个人在这个群体中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承担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居住在城市里的社区的共同体,平等协商的草案就显得有点粗糙。这里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平等协商形成了的共同体,一方面是赞同拆迁和不赞同拆迁的共同体之间的平等协商,另一方面是被拆迁人形成的共同体和拆迁单位或者政府之间的协商。草案没有提到共同体内部的协商的问题,知识提到了开发商之间的协商。但是现在存在合同失灵的现象,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会出现不能达成平等的协议的情况,政府使用强制拆迁的手段解决。现在将这种权利交给被拆迁人,让其之间协商,这种制度才是关键,也是被草案忽略的问题。
赵红梅:通过三位教授的发言,可以看出我们之间的共识:我们对政府粗暴干涉拆迁都保持了警觉,只是处理的手段不同。一种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制约政府,另一种是通过团体的办法制约政府和开放商,都可以继续进行探讨。今天这个研讨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自己也从三位教授的成熟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三位教授!